三个来自不同城市的年轻人,各怀心事,有人伤痛,有人茫然。他们在冰天雪地的边境小城相遇,一起在城市里漫游,之后又一起去长白山,碰到一只熊……
 【资料图】
【资料图】
这是电影《燃冬》的故事。导演陈哲艺开始准备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没有剧本,他写下的两页剧本大纲后,从新加坡来到中国,落地后防疫隔离了14天。疫情剥夺了太多对生活的掌控感,尤其对一个导演来说,被打回到生活之中的陈哲艺,说自己简直经历了一场“存在危机”。
《燃冬》海报
陈哲艺是那种结婚数年,仍被太太经常询问“我和电影到底哪个更重要”的人。他爱电影如命,却因为全球经历的公共卫生事件骤然被剥夺了一个“导演”的身份。而当人们的目光自然而然聚焦在线观影、短视频,越来越多的电影院接连关闭,各种项目接连取消的这些年,他“对不被看到的电影、不被看到的自己,都产生了存在焦虑”。这种焦虑催促陈哲艺去用实践证明,“我还会拍,电影还需要在那里,还会有人进影院看电影。”
陈哲艺导演的《爸妈不在家》获2013年第66届戛纳电影节金摄影奖(导演首作奖)
陈哲艺(中)携《燃冬》主演刘昊然(左)、周冬雨亮相2023年第76届戛纳电影节,该片入围“一种关注”单元
从完成《爸妈不在家》到如今的《燃冬》,陈哲艺正式成为一个长片电影导演,刚好十年了。他的电影作品数量不算多,但从处女作面世就摘下戛纳的金摄影奖起,陈哲艺一直被影坛视为亚洲青年导演的翘楚,六年打磨的《热带雨》同样横扫诸多奖项,扎实当代生活下细节里写满疲惫和疏离感的温柔,让陈哲艺收获众多影迷的同时,也让影评人给他扣上一个“成熟老灵魂”的帽子。
一直以来,他依照直觉创作,新加坡移民社会赋予他看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眼光,细致的观察力和超高的共情能力好像镜头理应记录下这样的人与生活。
《爸妈不在家》讲外劳菲佣和小男孩之间的情感,从中瞥见一个经济危机下中产家庭的压抑与焦虑;《热带雨》中马来西亚华文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禁忌与温暖,掩不住孤立无援的女性在家庭与社会生活中摇摇欲坠的底气;疫情之后,他去到欧美世界开始非华语电影的创作,《漂流人生》是非洲难民漂泊在希腊小岛回望战争和过往伤痕的挣扎。
他的电影里有时代和宏观视角织就的一张网,但最终都落在细致的个体情感体验之中。而《燃冬》,“老灵魂”陈哲艺,想让自己,去和当下的年轻人对话。
回到疫情隔离的日子,他有了大量的时间漫游在互联网上,他看到许多公众号和B站UP主的VLOG,看到年轻人陈述着自己内心的焦灼和丧气,“我看到的是一种不安、一种焦虑,我之前不是太了解,然后就一直在研究这件事情。”
《燃冬》剧照
《燃冬》是陈哲艺电影生涯上一次全新的尝试。这位热带长大的导演随性而至,踏上中国北方寒冷边陲的土地,他一如既往地在故事里融入了外来者视角、多元文化融合等创作母题。片中人物的境遇,如片名一般,是一次温暖与寒冷碰撞的超情感体验。
在今年戛纳的“一种关注”单元首映后,好莱坞电影媒体《The Wrap》称赞陈哲艺“创作了一首明亮发光的《祖与占》式的即兴演奏,既沉思又具有推动力”。陈哲艺喜欢法国新浪潮,在最初构想人物关系的时候想到特吕弗的这部代表作,也有看过电影的影迷观众戏称电影里三人行的关系是“戏梦东北”。三个人短暂相聚又别离,故事里,有人在爱,有人相爱,有人等待爱,有人拥抱爱。大多数时候的情感是欲说还休的暧昧不清。“这不是一部单纯、甜美的爱情电影。”陈哲艺在上映当天这样向观众解释这部电影。
《燃冬》剧照
这是他第一次带着自己的长片作品走进国内影院,选择了七夕的档期,大众对这个时段上映的电影有固有的期待。陈哲艺希望观众们能带着更开放和感受的心态进入这些年轻人的世界,“他们是三个独立的、年轻的、也渺小的个体,在心灵边境上寻找出路。我想要捕捉的状态跟情绪是没有答案的,可是它一定留下了什么,可以给人力量。”
另一个和以往截然不同的地方是,《燃冬》的自由和感性。找到周冬雨、刘昊然和屈楚萧三位演员的时候,他还没有完整的剧本。而放在过去,完美主义的陈哲艺,一个剧本至少都要打磨两三年。现场虽然并非即兴的发挥,但呼吸感极强的手持镜头对排演的捕捉,以及大量音乐调动的感性情绪推进都让他的电影较之之前的客观冷静,呈现了前所未有的饱满情绪张力。
“这是我做过最自由的事。”他这样形容这次拍摄。当他把这部电影形容为希望治愈当代年轻人的“一封情书”的同时,首先被这部电影治愈的是他自己——当他结束《燃冬》的拍摄,进入到《漂流人生》的创作中,他好像度过作为一个导演的“存在危机”,“我能看到那个更自信、更松弛的自己”,但同时,面对整个时代潮流的转变,创作者身在其中的无力感,似乎也和电影的主题和气质冥冥之中呼应着。
影片上映期间,导演陈哲艺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谈及这次特殊而自由的创作,以及当下阶段他对人生和世界的思考。
陈哲艺
【对话】
缘起一场隔离期间的“存在危机”
澎湃新闻:看到这部电影源起于你在疫情期间的憋闷,那是一个什么样状态?在那个阶段里意识到哪些之前没有意识到的事情吗?
陈哲艺: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存在危机,可能觉得自己差一点要放弃做导演了。那时我一直在家里,买菜做饭、带小孩、洗衣服。疫情期间我拍了一部很个人的短片《隔爱》,把我在疫情里的感触都拍出来了。
《隔爱》剧照
好像一个男人完全失去尊严的感觉,你失去了一种身份,一个创作者,电影导演的身份。当所有影院都关门,没有电影在拍摄时,你又是谁?那会儿我发现自己除了还会做饭以外,就没有其他的一技之长了。可能我勉强可以去电影学院教书,但我存在的意义在于什么?
而且对我而言,那时最大的一个打击在于所有人都开始看短视频和线上视频平台,我不确定疫情之后还有人会去影院里看一部我的电影,细致、克制又安静的电影。甚至现在疫情过后我还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可能所有观众的观影习惯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澎湃新闻:《燃冬》的主题和这段经历有关吗?
陈哲艺: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热带雨》2019年去了各大电影节,2020年发行,基本上也就是疫情那一年,当时几乎是它发到哪儿,电影院就关到哪儿,所以它是一个没有被看到的作品。
《热带雨》剧照
那时我在线上做映后,遇到很多观众会很意外,刚刚看的不是一个40岁中年女老师的危机吗?为什么导演看起来那么年轻?我就得到一些反馈说我拍电影好沉稳,很老成的感觉,也常会被问到为什么不去拍一个更年轻的,更自由的影片?
加上疫情在家没什么事情,在公众号、豆瓣上读了很多内容,看到很多年轻人都在抒发自己的情绪,也看了很多b站上的个人Vlog,带给我感触的是他们有很多迷茫、焦虑、困境,以及不安。所以我就试图了解这个群体,去拍一个三位受伤年轻人的故事,他们是怎样在短时间的相遇和旅途中彼此得到治愈。
《爸妈不在家》剧照
澎湃新闻:但其实《爸妈不在家》里有小男孩,《热带雨》里有高中生,你的电影里并不缺年轻人,《燃冬》和你之前的作品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陈哲艺:应该说《燃冬》从影像感到节奏,到音乐,跟我之前的作品都很不一样。看过《爸妈不在家》和《热带雨》的观众会发现这两部作品里是几乎没有配乐的。但《燃冬》我从创作之初就知道它需要用音乐去把很多情绪点出来,也很早就有配乐老师加入。我要一边拍一边把片段发给他,他来创作配乐,每晚我们都会通电话。
对这三个角色和影像的一些处理上,我会用更抽象的方式去把当代年轻人的几种困境讲述出来,它是跟之前的手法很不一样的,而像《爸妈不在家》《热带雨》,包括我的第三部电影《漂流人生》都是非常写实的影片。但这次拍《燃冬》我让自己用其他方式把这种情绪点出来,而且我想要捕捉到的状态和情绪是没有答案的,它本身就是很模糊的。片中这三个人在寻找一种灵魂上的自由,我也是一样,没有怎么去约束自己。
《漂流人生》剧照
澎湃新闻:所以“老灵魂”有投射自己对年轻的一种回望或是当时的一些状态吗?
陈哲艺:并不是我投射了自己的状态,反而是投射了我的另一种可能性。因为我的青春是没有那么的澎湃,那么轰轰烈烈地年轻过的。跟电影里比,我是比较乖巧的,25岁我就结婚了,也没有很丰富的感情史,没有那种纠缠的爱情,更没有去越界尝试一些比较危险的情感。所以我的青春算是蛮安逸的,但我又永远都会处在那样一种焦虑中。
《燃冬》剧照,浩丰(刘昊然 饰)
三个被打败的人,全世界的年轻人都有共鸣
澎湃新闻:三位演员他们一开始没有看到剧本就已经答应来演,拍摄现场是怎样的一个工作状态和氛围?
陈哲艺:他们三个人都很信任我,我们都很愿意去奉献,一起去冒险。工作上大家都很认真,但是认真之余,只要我们是在户外拍雪景,他们就会一直在玩雪,互相丢雪球。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挺认真的,也因为我拍片的时候很认真,很多时候导演的状态是会带动演员的状态的。而且我对他们很严格,要求特别高。
《燃冬》剧照,韩萧(屈楚萧 饰)
他们三个人用吉他弹唱的那场戏可能观众看起来很流畅自然,但实际上我们拍了很久,里面暗藏了很多情绪,并没有那么直接,要从前面周冬雨发酒疯到后面的一个转折,感受到心里面的伤痕,刘昊然在后面看着她也在感受这样一个情绪。
可能大家一直觉得这次的拍摄是很随意的,但我其实是一个超级无敌控制狂,我就是一个白羊座。所以它并不是所谓的“即兴创作”,在现场看到有什么东西我们就拍什么,它是有一定的筹备时间,当然会比较短。而且每天我拍一场戏,也都是有一个之前完整定制好的一个剧本,当然我们拍摄过程中也会有修改。
澎湃新闻:在你的构建里,为什么是这样三个年轻人,他们分别有怎样的代表性?
陈哲艺:我希望表现的是三个被打败的人,一个是被梦想打败的前运动员,从小只有这样一个梦,被培养,被挑选,但最后受伤退役,她不懂得如何接受这样的挫败,也不懂得如何面对家人和周遭的人。第二个是刘昊然所扮演的浩丰,被我们所谓的一种很传统的东亚的机制打败,从小被逼迫着读书,必须要上好学校,找到好工作,但当所有东西都做足了之后,却又没有存在感,很空虚。第三个就是由屈楚萧扮演的这个角色,他从小就无心上学,认为自己没有天分,不比别人好,干脆就不跟别人竞争了,还没被打败就放弃了,有点躺平的感觉。
《燃冬》剧照
澎湃新闻:作为一个有国际视野的导演看来,中国年轻人的状态是有特殊性的吗?
陈哲艺:我很意外的一点是,我们在戛纳首映时,有很多人甚至是意大利、北美、南美的媒体说看到了现在他们国家年轻人的样貌。而且我刚从澳洲的墨尔本国际电影节过来,我做了他们主竞赛单元的评委,也在那里放了两场《燃冬》。会有当地的一些00后,既有澳洲土生土长的学生,也有从东南亚过去念书的学生,其实我并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对浩丰有很深的感触。
所以我认为它不单单是中国年轻人的状态,它可能是现在世界上很多年轻人普遍的一种状态。特别是全世界物价越来越高,房子越来越贵,这是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去面对的。我们也现在处在一个网络时代,年轻人的成长完全是在网络时代下的,我是到12岁才接触到互联网,有了自己第一个E-mail,但我小孩6个月时就知道怎么按我的手机密码。他们所面对的世界和过去已经完全不同。
陪伴和懂得是有力量的,关系不必有答案
澎湃新闻:很多人看这个片子会想到《祖与占》,但那部影片里三人的情感纠葛的大半生,而《燃冬》是短暂的,你对这种关系的长久和短暂的理解是怎样的?
陈哲艺:我在创作的时候,一说要拍年轻人我就想到特吕弗的《祖与占》,我重新去看了一次,看它是如何建构整个故事的,里面的人物线是怎样的,但并不是说我要再拍一部《祖与占》。其实另外我还考虑过一部让我很感动的电影,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英国导演,叫安德鲁·海格,他拍摄了一部同志电影《周末时光》,就是两个男生在一个周末遇见彼此并发生关系,但周末之后其中一个就要去美国念书或工作了。是会有一种不舍,但是你又记住了短暂的美好。
《燃冬》里的三个人在短暂取暖后,谁也不会为谁停留,但他们在彼此身上留下了一些东西。而且我认为这样的关系它不应该是永恒的,如果这三个人的关系是永恒的话,它不会是美好的,反而是因为它的短暂存在,所以留下了一些美好。
陈哲艺(右)在《燃冬》片场
澎湃新闻:影片中每个人的困境其实都是无解的,怎么理解最终各自上路的力量感?
陈哲艺:在我看来,很重要的是他们互相得到了一种关怀,很多时候不是要去寻找答案,而是知道有人在关心你,这是可以给人力量的。而且我算是一个乐观者,我的所有电影的结尾,甚至是《热带雨》,主角到了后面是很凄凉的,但她还是有一种温度,我相信人生还是有希望的,无论现在多黑多暗,都还是会有曙光。
澎湃新闻:东北是整个电影里非常重要的“角色”,环境在你创作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陈哲艺:我的作品一直都是外来者的视角,所以这三个角色我也把他们设定为外来者。虽然我们去了东北,但没有让任何角色是东北人。我去了东北后把很多细节写了进去,虽然从小到大从来没这么冷过,但反而我看到的和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温暖”,我真的很意外。所以我把延吉和长白山拍得挺浪漫的,大家可能在影视上对东北的印象肯定不是这样的,都是比较破旧落后,脏一点的感觉,很多犯罪片发生在这里。但我看到的不是这样。
《燃冬》剧照
包括片中一直出现的冰块,一开始我就一直在想我们要拍一个冬天的故事,可能一提到冬天一下子就会想到下雪,但我会认为雪已经被拍得太多了,而且太浪漫化了,所以我就想到冬天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是冰。于是就秉着这个概念,去想它怎么结成冰的过程,只要0摄氏度以下可能两三个小时就会结成冰,但这块冰拿出来,一点阳光,一点温度,它又化成了水,我就想用它来表达这三个人的结论,在很短的时间内,像仲夏般浓烈炽热,又很复杂的情感,但很快它又消失融化了,却又肯定在他们彼此内心中留下来了。
澎湃新闻:影片中有几场情欲戏,大家也会讨论在国产院线里算是“大尺度”,但在你一贯的创作中,情欲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欲望”在你所理解和构建的人的生活和困境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陈哲艺:我认为两个灵魂一旦真的有一个很深入的交集,它就会有一种肢体上的一种亲密。这就好像为什么我会想要抱我的小孩?我可以就一直坐在那,顺着他就好了,但为什么我会想要抱他?我认为人与人之间只要产生了灵魂上的连接,他们就会有更进一步的互动。
《燃冬》里最后浴室的那场戏,我记得我写它的时候就是欲望与理性的挣扎,因为浩丰知道他要走。所以这场戏其实拍的是离别,他知道这段关系不可能是永久的,而是短暂的。浴室里的那场戏是我整部电影最喜欢的一场戏,它交集了很复杂的情绪。
《燃冬》剧照,娜娜(周冬雨 饰)
澎湃新闻:熊的意象该如何去解读?
陈哲艺:我非常喜欢长白山,真的是被长白山天池迷倒了,就想把结尾安排在长白山。于是搜了很多关于长白山的故事,找到了一个朝鲜族的非常有名的传说,熊和老虎的故事,我就很想把它拍出来。而且我会觉得他们最后的所谓治愈应该来自一种和更大的力量,和大自然的相遇,所以就让他们碰到一只熊。而且我在写的时候,我认为它是人与动物很特别的一种心灵互动。这只熊嗅得到她的伤口,也嗅得到她的伤感,她的创伤。熊是懂她的,天地是接纳她的。
《燃冬》剧照
爱的定义没有这么简单
澎湃新闻:这种更加开放和自由的,若即若离的情感状态在当代人的生活中非常常见,但主流电影观众似乎也遵循某种更“正确”的幻想,影片选择在七夕上映,是否担心它和观众对爱情电影的期待有所冲突?
陈哲艺:我已经给自己打了很多针强心剂了,我是希望观众抱着一个更开阔豁达的态度和心境去看这部电影。因为我觉得爱的定义没有那么简单,甚至情感本身就不简单,它没有所谓的黑与白,我所有的电影里的情感都一样复杂。
《爸妈不在家》当中的菲佣跟男孩既是一个保姆跟雇主之间的情感,又像是友情,也会有点像妈妈跟小孩的亲情。但在拍他们玩的一场戏中,我会觉得这男孩是不是爱上她了,又感觉好像是他的初恋一样,所以离别时才会那么深刻。《热带雨》也一样,老师跟学生之间真的是爱情吗?它也不是友情,那是母子之情吗?好像也不是。甚至你看《漂流人生》,这两个人你说它是爱情吗?但又感觉它超越了友情,但我又不认为它很直白的就是她们恋爱了。
所以我每次看人的情感,情绪,人与人的关系时,我都不会带着一种道德批判,或是一种所谓的主流价值去看待它。因为人为什么会有意思?就是因为人实际上是没有所谓的黑与白,它都是处在一种灰色地带。
《燃冬》剧照
澎湃新闻:拍完这部电影,你就很快就又投入到《漂流人生》的创作过程当中,经过《燃冬》这样一个很不一样的创作方式之后,它对你后面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陈哲艺:《燃冬》让我找到一种自信,我发现原来我还是有功底的,在就地取材编写一个故事时,怎么去用这些不同元素建构一个完整的故事线、人物线。现场在没有做太过细腻的分镜的情况下,要怎么把这些情绪处理好。我突然就会相信自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以前我会一直担心,要把一切准备好,弄得非常准确,而我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更自信更松弛的自己。
澎湃新闻:是不是解放了一点你的强迫症,以后不用花三年写剧本了?
陈哲艺:那我希望以后我不用自己写剧本了,因为太苦太累了,苦是因为我每次写一个故事我会很靠近里面的人物。不过其实拍《漂流人生》时,它的创作方式又跟之前一样,也是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去改编小说,筹备拍摄。我在创造剧本时,它的镜头语言就已经确定是那样的了。同样的为什么《燃冬》的镜头语言会有不一样的味道,因为它在创作方式上就不一样。
《漂流人生》剧照
不过我有在想,如果再拍那么多像《漂流人生》这样里面那种悲惨的事件,我不确定我会不会患忧郁症,甚至自杀,因为很多时候我带入太多情感到一个作品里。所以我下一个尝试可能会是拍一个喜剧,虽然“喜剧的内核是悲剧”,但至少拍摄过程中可能会笑得比哭得多。
澎湃新闻:你前面说你自己会焦虑于电影的某种“消亡”,现在整体的票房大盘又好了,你的创作也接连启动,这部分的焦虑被治愈了吗?
陈哲艺:最近的状态也是很焦虑。并不是因为电影上映,我还是会在想电影的时代是不是改变了?电影院里是热闹了,但它们都不是我自己会特别向往的那种电影。我会想我喜欢的影片,是不是在这个时代里不会得到足够的理解跟共鸣?我开始有点丧了,我是一个从来不会想“躺平”的人,但最近我真的有在考虑这件事情。躺平以后我就做饭,带小孩,我可能会教育他,不要拍电影,不要爱上电影。
关键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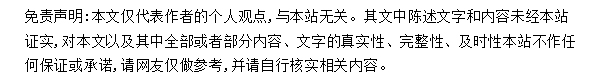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