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经典文化出版了作家康夫的《朝阳南路精怪故事集》。这本书中,康夫延续古典志怪传统,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建构了新的中国本土城市奇谭。作品虽以“精怪”为主角,却聚焦在城市与人的生活百态上,有着细致入微的对现实的观察。相较于前作《灰猫奇异事务所》的幽默轻盈,《朝阳南路精怪故事集》中更多地写及成年人的困顿——不上不下的事业、被催婚、恐婚恐育、缺爱的家庭等等,在魔幻的每一天里,作者虚构了一个又一个的精怪,尝试用魔法打败魔法。
最近,《朝阳南路精怪故事集》分享会举办,本书作者康夫与《中国奇谭:乡村巴士带走了王孩儿与神仙》的导演刘毛宁、《智族GQ》报道总监靳锦展开对谈。三位嘉宾与读者一起漫谈城市文明中消失的精怪文化。
几乎每个人都曾在精怪故事的陪伴中长大。在人们的印象中,精怪故事多发生于山野村落;但在城市中,尤其是现代化城市中,很少有关于精怪的传说。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在康夫看来,城市精怪文化的缺失,一方面是因为城市化的时间并不长,相较于悠久的农业文明,城市还没有形成足够的条件来孕育精怪故事。另一方面,“城市”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地点,而是现代人追求职业理想、生活理想的目的地。节奏快、压力大,这几乎成为了城市生活的标签。面临重重的现实压力,人们很难再把所剩无几的精力分配给想象力。
“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拆解,也很难形成以前的群体性共识或精神寄托了。”刘毛宁剖析道。靳锦也认同这一观点。“在古代,‘精怪’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我们对某种意识、理念的拓展,精怪故事是古人对于更公平的社会的设想。”靳锦补充道,“但工业化文明的历史较短,发展太快,现在的我们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好像不依赖精怪了。”
《朝阳南路精怪故事集》则尝试在精怪文化相对贫瘠的现代城市中建立精怪的传统,在序言中,康夫写道:“在我看来,有精怪参与的生活比只有人类的生活有趣得多,有精怪出没的城市也比单纯的人类城市更吸引人。人们害怕精怪的神秘与危险,然而真正遇到过它们的人类往往将其当作奇妙而珍贵的经历。国贸一家快餐店的老板,曾经被一只姜黄色的猫请去切磋厨艺;除夕雪夜的高速公路上,有人遇见过某种动物经营的快递车辆;还有人曾收到老鼠送来的一捧黄金……倒霉的也不是没有,有一家开连锁果汁店的,为了省钱雇了一群浣熊洗水果,最后险些无法收场。”
在康夫的故事中,她借“精怪”之眼,提供了看待城市的另一种视角——城市不再是钢筋水泥,它被丰富拓展,拥有了更多奇妙的属性。这书中,精怪化身成人类的模样,生活在城市之中,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有的在北京虎坊桥开酒吧,有的在长沙太平街做婚介,还有的就在加班族出没的中关村地铁口支一个小面摊。
作为小说的核心设定,“朝阳南路”是书中唯一一个虚构的地点,它汇集了所有精怪故事,如同“九又四分之三”站台,打通真实与奇幻的边界。康夫说这一构思的灵感源于自己多年的“京漂”经历:“‘朝阳南路’与真实的朝阳北路相呼应。这里会集合我们所有的想象、我们所有的愿望、生活中所有的奇遇、快乐等等,是可以抵达的彼岸。”她希望借此创造一个城市精怪的乌托邦,为忙碌疲惫的都市人留下一片可以自由幻想的区域。
在以往许多作品中,精怪对人往往有很明显的情感趋向,比如憎恶人类、贪恋人类,或者想成为人类。而在《朝阳南路精怪故事集》中,精怪与人的关系则要“清淡”很多:精怪生活在人群中,却不打扰人类,只是做一些小本营生;“他们”只在人类失意的时刻找上门,提供帮助,建立一次短暂但深刻的联系,然后又很快地消失。康夫笔下的精怪和人之间有一种疏离感。
康夫对这样的关系作出了解释:“这种疏离,实际上是现代城市人本身状态的映照,也是大多数人对一种理想人际关系的投射和向往。”在刘毛宁看来,精怪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的外延,其作用是帮助人解决无法完成的事、无法消解的矛盾。靳锦则从书中看到了精怪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陪伴关系,但更简单,不会让人有负担感。
“精怪文化能够承载虚构的一切。”靳锦表示,人们需要有一个充满无限虚构性的地方,来滋养、放飞想象。在这里,现实的时间停止了,一切不再按部就班,而是跳跃的、自由的。这也是当代人喜爱精怪、需要精怪的原因。
同为青年创作者,刘毛宁与康夫惺惺相惜。他执导的《中国奇谭:乡村巴士带走了王孩儿与神仙》中,展现了这样一个事实: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孩子的童年、人们的想象力、曾经的精神寄托都渐渐消失了。在两点一线的现代生活中,人们更需要属于城市的精怪文学。
活动现场
城市精怪文学不是让人们相信精怪的存在,而是让精怪的存在,为人们开辟一个精神避难所;它拓宽时间、空间的维度,让“压力山大”的现代人有喘息之机。“城市的发展无可厚非,这是人们的需求,但想象的力量能让人们意识到世界的丰富、生命的多层次。”刘毛宁说,“我们需要找到城市文化与精怪文化之间的契合点。”
在《朝阳南路精怪故事集》中,康夫努力寻找的,正是这样一个契合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关键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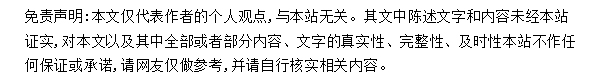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